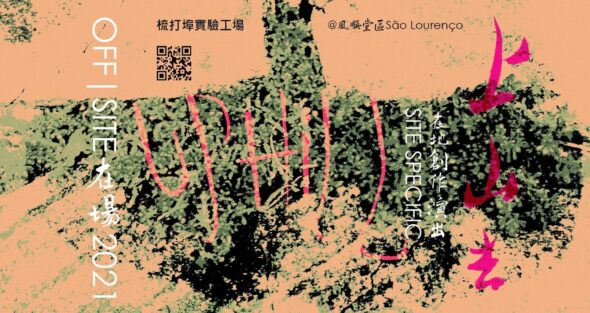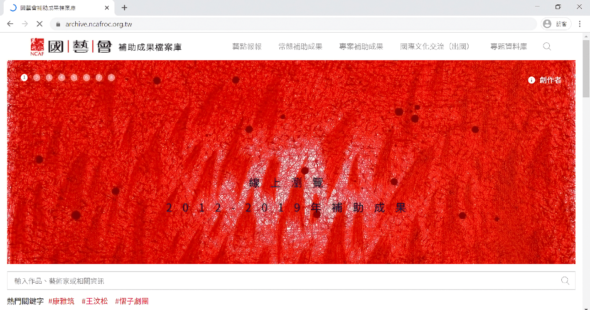對南非的「種族隔離政策」無知,成為我的視界的局限。對自身所在的社會的有感無力,亦是我對的想法的局限。我只能在這兩局限之間,去看Peter Brook的《情人的西裝》(The Suit )。
妻子外遇的兩種眼光
丈夫發現妻子有外遇,回家發現一套第三者留下來的西裝,
丈夫、妻子、第三者,我想起張愛玲編的《太太萬歲》。為甚麼太太會被認為是萬歲?丈夫創業沒錢,太太便去娘家跟父親要錢;丈夫有了一個很麻煩的外遇女友,太太起初假裝不知道,最後去給他斬斷煩惱絲;因情傷提出離婚,最後丈夫隨便道歉便嫣然一笑重投丈夫懷抱,和好如初;有這樣的太太,每一個丈夫都會高呼萬歲,萬歲,萬萬歲。
反之,如果太太別有情人,那是甚麼?這還用說,是潘金蓮,是閻婆惜。
成長於戲曲臉譜的價值觀之中,不管對台上角色、政治人物、還是街坊鄰里都是非忠即奸、非黑即白。沒有人去可憐《太太萬歲》裏上官雲珠演的妓女咪咪為何如此坎坷,也沒有人可憐潘金蓮的出身,和對她自身可憐之處有所感懷。
看完《情人的西裝》後,與多位友人討論,感受到強烈暴力的人,好多都是女性,或者在敏感於女性處境的人,也或者是可以接受和太太離婚再見亦是朋友的現代人。
當女主角將絲巾——作為和丈夫共同建立家庭,在每天一同吃飯桌上擺設的生活物件——放入情人西裝的口袋裡,上這一刻,家庭已經容下了第三個人。在我們社會中的「潘金蓮」已經出現。
潘金蓮在中國舞台上,千年裏死了無數次,大家都拍手稱快,如果有人為潘金蓮的身世可憐,覺得她是情有可原的,即使有,也只會是少數。根據我媽媽的師奶級觀點,她對潘金蓮的定論是︰「是很慘,不過即使出身不好,有了老公就應安份守己,就算退一萬步,有人喜歡她,也不要殺了自己的老公嘛……」偷漢可以理解,殺了丈夫不應該,那因為偷漢而殺丈夫又能不能理解?偷漢和殺丈夫是不是要分開看待?如果偷了漢不殺丈夫,偷漢是不是可以因為其出身卑賤,難得有帥氣又多金的西門慶包養,得以脫離那個生活在社會底層在街市賣炊餅的怪人武大郎,而可以原諒?或者更現代一點,就移情別戀應該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地分手?就潘金蓮偷漢該殺不該殺的問題,邏輯好像越說越是混亂,千年也說不清。
回到《情人的西裝》,我們看到Matilda因為「偷漢」(在現在自由戀愛的環境下,應該正名不是偷漢而稱之為「另有感情」)而遭受痛苦,畢竟婚姻觀念進步了,但父權的復仇卻仍在存在。雖然沒有殺潘金蓮的拍手稱快,但對妻子的不忠的反擊,看來好像不覺得有甚麼兀突和稀奇。丈夫Philemon的手段只是另有不同而已。
受暴者如何感知暴力?
後半部份,丈夫Philemon對Matilda施展「暴力」成了重點。敏感的歡眾,關注著二人無聲的暴力。Matilda到的羞辱,只存在她與丈夫之間︰吃飯時丈夫以禮待第三者的西裝,叫妻子拿著西裝在街閒逛。暴力起初存在丈夫向妻子的方向,和妻子心裏與外界的看法之間,最後剩下丈夫形單隻影承受。這對夫妻沒有在街上扭打,沒有當眾揪頭髮、扯衣服,對Matilda實施群眾路線、Matilda沒有罵街。真實比戲「好看」,臨近城市中,被遊街、被當眾羞辱,視作等閒,如新聞裡的性工作者和嫖客被拉去遊街示眾【註1】,到現在都沒有對被拉去遊街的人作出平反和補償。舞台外的現實中,遊街示眾也可以不了了之,戲中深層而且內化的暴力,就會被視作不嚴重的暴力。
無言的暴力,如沉默的冷戰,比打個皮開肉綻頭破血流高明,那麼丈夫將妻子企圖於枱面上極力隱瞞維持原有局面的假氣氛撕開,對奸夫施以羞辱式的歡迎,讓受暴者會更受到毀滅性的傷害,更是絕招、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。戲中的暴力可以成為各種隱喻,但前提是,施暴者先得確認,受暴者必須是擁有可供破壞的人格主體,尤其要敏感到用非肢體式暴力,只是用甜美的恥笑就可用達成攻擊的效果。
位在不同的社會語境裡,Matilda的不幸和潘金蓮到底有沒有可比性?潘金蓮必然不會視自己為受暴者,所有的壓迫造就她後來理所當然的命運。無法擁有完整人格的自省,是她和Matilda最不一樣的地方。被奴役之際,難以進行內在的思辨,或說難以看清自身的不堪,進而感到被羞辱,這些「缺乏」,造就中國戲劇中的女性受暴者「豐富」卻又「片面」的形象。但在現實之中,這樣的角色比比皆是,戲劇塑造了單一人物的性格審美,還是戲劇忠實地反映社會了對於人性辨析的單一面向(例如非奸極惡,非黑即白)?我很好奇,慣性評價潘金蓮的觀眾,在《情人的西裝》裡,如何能感受到Matilda所受到的暴力?
我很好奇,在武大郎對潘金蓮心生怨恨之時,潘金蓮真的感覺不到被羞辱嗎?潘金蓮在王婆茶店家回來給武大郎做飯,看到早上聽完鄆哥的流言蜚語臉色青綠的武大郎,會不會也同樣感到受傷?還是,潘金蓮根本不在乎這點眼色,只有在死到臨頭的時候,有些懊悔,因為畏懼著在武大靈堂上,武松的刀將朝自己頸上砍去。
「Forgive and forget」向來都是當下、即刻被發生的事情,而壓迫正在進行,現實中的受迫者,沒有完整的人格主體,所以也不被感知、無法反省,難以自覺,只有忠於自己的奴性。最惡劣的狀況,什麼地方都一樣,從沒改變。
註1︰深圳捉妓女嫖客游街惹争议 北京究责 妇联抗议
http://www.boxun.com/news/gb/china/2006/12/200612061632.shtml